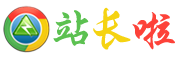首页 > 房产
神木租单元房包家具
惠阳淡水只租一个月一房一厅包家具的套房?
在淡水只租一个月就能退房的且包家具的一房一厅套房几乎没有。
要找转租才行,会有少部分租户由于有事需离开一两个月而居住时间未满合同时期转租,价格会比原价低一点。
最好是朋友转租或介绍的转租户。
带家私的一房一厅套房至少签半年合同,交两个月房租,其中一个月的算押金。
神木幸福家园的房子什么时候可以出售
展开全部 原文: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欧·亨利(著 )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
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
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
他们用爵士乐曲调唱着流行曲“家,甜美的家”;全部家当用硬纸盒一拎就走;缠缘于阔边帽上的装饰就是他们的葡萄藤;拐杖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这一带有成百上千这种住客,这一带的房子可以述说的故事自然也是成百上千。
当然,它们大多干瘪乏味;不过,要说在这么多漂泊过客掀起的余波中找不出一两个鬼魂,那才是怪事哩。
一天傍晚擦黑以后,有个青年男子在这些崩塌失修的红砖大房中间转悠寻觅,挨门挨户按铃。
在第十二家门前,他把空当当的手提行李放在台阶上,然后揩去帽沿和额头上的灰尘。
门铃声很弱,好像传至遥远、空旷的房屋深处。
这是他按响的第十二家门铃。
铃声响过,女房东应声出来开门。
她的模样使他想起一只讨厌的、吃得过多的蛆虫。
它已经把果仁吃得只剩空壳,现在正想寻找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充空间。
年轻人问有没有房间出租。
“进来吧,”房东说。
她的声音从喉头挤出,嘎声嘎气,好像喉咙上绷了层毛皮。
“三楼还有个后间,空了一个星期。
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她上楼。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线微光缓和了过道上的阴影。
他们不声不响地走着,脚下的地毯破烂不堪,可能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要诅咒说这不是自己的产物。
它好像已经植物化了,已经在这恶臭、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茂盛滋润的地衣或满地蔓延的苔藓,东一块西一块,一直长到楼梯上,踩在脚下像有机物一样粘糊糊的。
楼梯转角处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
它们里面也许曾放过花花草草。
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花草已经在污浊肮脏的空气中死去。
壁龛里面也许曾放过圣像,但是不难想象,黑暗之中大大小小的魔鬼早就把圣人拖出来,一直拖到下面某间客房那邪恶的深渊之中去了。
“就是这间,”房东说,还是那副毛皮嗓子。
“房间很不错,难得有空的时候。
今年夏天这儿还住过一些特别讲究的人哩——从不找麻烦,按时提前付房租。
自来水在过道尽头。
斯普罗尔斯和穆尼住了三个月。
她们演过轻松喜剧。
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也许你听说过她吧——喔,那只是艺名儿——就在那张梳妆台上边,原来还挂着她的结婚证书哩,镶了框的。
煤气开关在这儿,瞧这壁橱也很宽敞。
这房间人人见了都喜欢,从来没长时间空过。
” “你这儿住过很多演戏的?”年轻人问。
“他们这个来,那个去。
我的房客中有很多人在演出界干事。
对了,先生,这一带剧院集中,演戏的人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住。
到这儿来住过的也不少。
他们这个来,那个去。
” 他租下了房间,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
他说他很累,想马上住下来。
他点清了租金。
她说房间早就准备规矩,连毛巾和水都是现成的。
房东走开时,——他又——已经是第一千次了——把挂在舌尖的问题提了出来。
“有个姑娘——瓦西纳小姐——埃卢瓦丝·瓦西纳小姐——你记得房客中有过这人吗?她多半是在台上唱歌的。
她皮肤白嫩,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金红色头发,左眼眉毛边长了颗黑痣。
” “不,我记不得这个名字。
那些搞演出的,换名字跟换房间一样快,来来去去,谁也说不准。
不,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
” 不。
总是不。
五个月不间断地打听询问,千篇一律地否定回答。
已经花了好多时间,白天去找剧院经理、代理人、剧校和合唱团打听;晚上则夹在观众之中去寻找,名角儿会演的剧院去找过,下流污秽的音乐厅也去找过,甚至还害怕在那类地方找到他最想找的人。
他对她独怀真情,一心要找到她。
他确信,自她从家里失踪以来,这座水流环绕的大城市一定把她蒙在了某个角落。
但这座城市就像一大团流沙,沙粒的位置变化不定,没有基础,今天还浮在上层的细粒到了明天就被淤泥和粘土覆盖在下面。
客房以假惺惺的热情迎接新至的客人,像个暗娼脸上堆起的假笑,红中透病、形容枯槁、马马虎虎。
破旧的家具、破烂绸套的沙发、两把椅子、窗户间一码宽的廉价穿衣镜、一两个烫金像框、角落里的铜床架——所有这一切折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舒适之感。
房客懒洋洋地半躺在一把椅子上,客房则如巴比伦通天塔的一个套间,尽管稀里糊涂扯不清楚,仍然竭力把曾在这里留宿过的房客分门别类,向他细细讲来。
地上铺了一张杂色地毯,像一个艳花盛开的长方形热带小岛,四周是肮脏的垫子形成的波涛翻滚的大海。
用灰白纸裱过的墙上,贴着紧随无家可归者四处漂流的图片——“胡格诺情人”,“第一次争吵”,“婚礼早餐”,“泉边美女”。
壁炉炉额的样式典雅而庄重,外面却歪歪斜斜扯起条花哨的布帘,像舞剧里亚马逊女人用的腰带。
炉额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物品,都是些困居客房的人在幸运的风帆把他们载到新码头时抛弃不要的东西——一两个廉价花瓶,女演员的画片,药瓶儿,残缺不全的扑克纸牌。
渐渐地,密码的笔形变得清晰可辨,前前后后居住过这间客房的人留下的细小痕迹所具有的意义...
猜你喜欢
- 最近发表
- 推荐